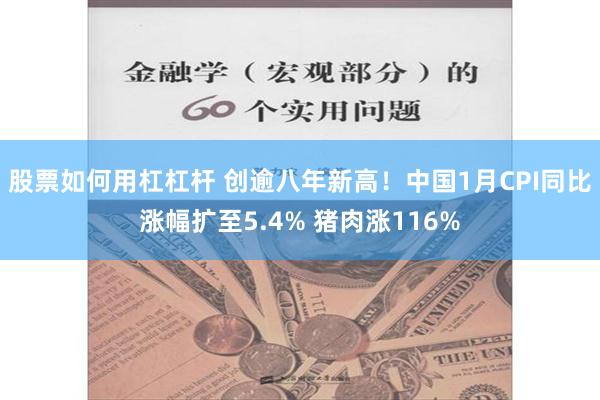“树林真可爱,幽暗而深远。/可是我还得赶赴一个约会,/还得赶好多里路才能安睡,/还得赶好多里路才能安睡。”(方平译)这首诗已经铭入了美国人的“文化无意识”,最后重复的两句,人人都能吟出它的英文原文:“And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/And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.”联邦快递把“Miles to Go”印在自己的车厢和包装上,“Easy Wind and Dawny Flake”(方平译为“一阵微风吹过……一片鹅毛似的雪花卷过”),则是烘干机、洗衣皂的现成的广告词。
你在不经意之间,就能在美国商场的货架上、在各色各样的商品的包装上看到这首诗,它的题目“Stopping by Woods on a Snow Evening”,方平先生译为《停马在雪夜的林边》,也许另一个常见译法“雪夜林中小驻”更精炼,而且“驻”字依靠其偏旁,恰可以解释为“停马”。这首诗,是罗伯特·弗罗斯特1923年发表的诗集《新罕布什尔》中的一首,次年,他凭藉此诗集获得了普利策诗歌奖。这之后,他又得了三次普利策,分别在1931年、1937年和1943年。弗罗斯特生于1874年,纵览整个20世纪,如果他不能称为“美利坚民族诗人”,那绝没有第二人可以当此名号了。

乡村、森林与雪夜
技艺高超的简洁,令弗罗斯特的诗篇俘获人心,也使中文译家犯难,中文在面对这种既精炼又“朗朗上口”的外语诗时是最笨拙的,原作的格律整齐和语词精炼,对于中译来说,几乎不可能兼得。《雪夜林中小驻》是从一个夜行人的内心视角出发写的,他把马停在树林间时,看四下无人,而马摇了摇胸前的挂铃,看样子也不知道主人为何停留。弗罗斯特用了4段16句诗行记下这一刻。无数中国人,在通过“床前明月光,疑是地上霜”认识中国古诗的时候,也接受了“疑”带来的不确定的美学,而近一个世纪以来的美国人,在做学子的时候,都是通过这16句第一次认识了自己国家的诗歌,通过弗罗斯特的第一句“Whose woods these are, I think I know. His house is in the village though”,他们能懂得,诗并不是简单的“有话不好好说”,而是在确定和不确定之间产生的叙述,是在转折、变换、交错之中发现韵律。
诗有名了,研究和评论就会特别细,牵扯出的主题也是足够宏大。这首诗,弗罗斯特是花了20分钟写成的。1922年,他在沙夫茨伯里的家中苦思一首长诗而不得时,突然在黎明的曙光中获得灵感,脑海中出现了冬日雪夜里一个驻马人的场景,从而落笔写下。场景很小,思绪和感受简短,但研究者、评论者说它达及生死之问,雪夜林间,也许为了欣赏风景,但也是因为困乏,而“赴约”是为了“安睡”,这意象总让人浮想到对死亡的暗示。如方平先生就这样解析:
“人生在世,好比百年过客,他的最后归宿就是那长眠不醒的死亡。对于那步履沉重、失去了生活勇气的人,他会产生一种幻觉,似乎听到了死神在发出引诱的歌声,使他像游子归家似的渴望早早结束那遍地荆棘的旅程。”
当然,弗罗斯特会否认这种解读。“安睡”“睡眠”的含混不清,正是一首诗的妙处所在,反映了诗人了不起的“伎俩”。弗罗斯特在说起此诗时,都说那是他“最好的回忆”,他也为此而得意。他把自己的诗歌视为表演,在许多演讲场合朗读自己作品时,他很需要、也无比享受在场者跟着一起吟诵的场面。他甚至说,自己某次演讲,对听众说:“你们有多少人不知道《雪夜林中小驻》?”现场两三千人中“只有一个人没羞没臊地举起了手”。
应该说,这位一生主要在乡村生活的诗人,对森林、雪夜的意象是太熟悉了, 因此他能很自然地织入隐喻,利用景物描写自如地调动读者的想象。像是他最早的一首诗《男孩的意愿》里也这么写:
“我的心愿之一是那黑沉沉的树林,/那古朴苍劲、柔风难吹进的树林,/并不仅仅是看上去的幽暗伪装,/而应伸展延续,直至地老天荒。//我不该被抑制,而在某一日,/我该偷偷溜走,溜进那茫茫林间……我看不出任何理由要回头返程……”
为“正常人”写诗
1912年8月23日,年近不惑的弗罗斯特,觉得自己在美国始终只是略有薄名,于是卖掉了新罕布什尔的自家庄园,携妻子和4个孩子从波士顿出发,渡过大西洋到英国,想做奋力一搏。他带在手头的作品,首先就是这首《男孩的意愿》。他拜访伦敦的文学大佬,把自己的诗作投给那里的杂志和出版商,两年以后,他拿出了一组新写的诗歌,取总标题为《波士顿以北》。这本诗集里的诗,一改《男孩的意愿》等早期诗里充满景物描写的风格,而是大量地叙事,讲故事,对话滔滔不绝。集子里的第一首就是《修墙》,以下仍是方平的译文:
“准是有谁不喜欢有一道墙吧——/让冻结的土地在墙脚下隆起,/大白天,叫垒石从墙头掉下,/裂开一个缺口,两人并肩走得过。/那猎人干的事却是另一番糟蹋,/我跟在他们后面,去做些修补;/他们不留一块垒石在石头上,/一心要把兔子从藏身的地方赶出来,/去讨好那群汪汪叫的猎狗……”
《修墙》说的是互为邻居的两户人家,因为院子之间的隔墙坏了,相约一起修墙,他们把掉地上的垒石捡起来,砌回去,干着干着,对墙产生了疑问:“我垒一道围墙,先要弄明白/我围进来的是什么,圈出去的又是啥?/我有可能冒犯的究竟是哪一家?/准是有谁不喜欢有一道墙吧……”诗中还有这样的幽默:
“墙就在我们并不需要墙的地方。/他那边,一片松树;我这里,苹果园。/我这些苹果树永远也不会踱过去,/吃掉他松树底下的球果。”
弗罗斯特的早期诗得到了叶芝和艾兹拉·庞德的欣赏,这二位当年是英语诗歌执牛耳之人,尤其是庞德,他和弗罗斯特之间的差异太大,前者是晦涩的现代诗的先驱人物,不但诗文中密集用典,写着写着还冒出个汉字来,而弗罗斯特却是字里行间一派“土气”的新英格兰诗人。庞德年轻成名,他对弗罗斯特的认可不无开恩的用意,也因为性格高傲,他一向居高临下地谈论弗罗斯特。弗罗斯特在有了名气以后,也很清楚他同现代派诗人之间是有一道消除不了的界线的,他维护它,就是在维护自己的美学。
在1955年6月30日布雷德洛夫英语学校的讲演中,80岁的弗罗斯特说:“谁有权随心所欲地把玩我的诗——就是那些能按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它们的正常人。”他说他为“正常人”而写,诗是“实际说话之语音语调的复制品”,正常人能够像欣赏有旋律的音乐一样欣赏一首他的诗,而不去辩论其中的深刻涵义。
对于“过度解读”,弗罗斯特逮住机会就要说上一通。《雪夜林中小驻》,因为太有名、场景感又太强,有人就问诗人说:雪落在林中,覆在树上,到底盖了多厚?这问题堪比对杜甫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的那种“解读”:“‘吹我屋上三重茅’表明杜甫的居住环境还不错,因为穷苦人家屋上只有一重茅”。对诗的夸张的“较真”,有时是琐谈戏言,有时却是要做正式的学术文章的。弗罗斯特谈到,有一位学院的院长,拉着他的手,跟他说《修墙》是一首“真正超越国界的诗”:
“只是为了逗逗他,我问‘你是怎么知道的?’我说我认为我对墙两边的人不偏不倚——只能算超越了墙界。‘哦,不,’他说,‘我能看出你站在哪一边。’于是我说:‘我越是说我,我就越是在指别人。’”
世上有两种现实主义者
他在英国大大载誉,他诗中的“质朴”(simplicity)收获了众口一词的称赞。在英国他最好的同行朋友,也是最能欣赏他的人,是爱德华·托马斯,这个人存诗不多,1917年才不到40岁就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,但是诗行词句同样简练质朴,而且,酷似弗罗斯特,托马斯也看重在自然景观中行走或驻足时,蓦然的发现与“惊奇”。
托马斯的诗中写过这样的意象:循着一些疏密不均的枝条步入小径,片刻后回头却见一片深林;一边走,一边计数着脚下的卵石,不觉抬头却看到自己上了一座桥。有时候,拿不准那到底是不是深林,或者,那桥是否其实是一条下边被冲出了河水的路。
在《失去了才明白》这首题目一目了然的诗里,托马斯讲到了一片一向走过的矮树林,在被砍伐之后才被“我”注意到,“如今地面光秃秃像一块骨头”,连砍下最后一棵柳树的伐木工“连同他的账单”都不知何往。树木变成了柴捆堆,然而“我”并未停留于神伤,而是望见一条露出的小溪,那是一个“支流的支流”的源头。这几乎就是《雪夜林中小驻》的美学流程,或者也可以对照弗罗斯特的另一首太过知名的诗——《一条未走的路》:
“深黄的林子里有两条岔开的路,/很遗憾,我,一个过路人,/没法同时踏上两条征途,/伫立好久,我向一条路远远望去,/直到它打弯,视线被灌木丛挡住。//于是我选了另一条,不比那条差,/也许我还能说出更好的理由,/因为它绿草茸茸,等待人去践踏……”
“伫立好久”,然后远望一番,踏上另一条路。越是这种似乎什么事都没干的场景,越是有引人入胜的余味。乡野的事物尽数进入他的诗篇,苹果、无花果、葡萄、白桦树,铁杉、槭枫,女巫,摩门教徒,种种恐怖的睡前故事和无名墓地……眼皮上积了白雪的马匹在牧场上跑,砖瓦匠在鸟鸣声中独自上工。当雪山在春天融雪,千万条银蛇从山顶滑奔而下,“只有月亮能阻止这混乱”,而当冬季的第一场雪落下,地面仍然干燥温暖,雪花为了润湿土地而前仆后继。

19世纪以来,英美两国的文人多有在大西洋两岸两头跑、混名声的,比如苏格兰出身的作家、批评家托马斯·卡莱尔,就是借重了美国思想界领袖人物爱默生的力量,才在伦敦获得了他想要的地位。弗罗斯特从英国回来时,他的《波士顿以北》已经有了美国版,在报亭和杂志摊上,评论他的诗歌的文章举目可见,而且评论的作者中不乏他一向看不上眼的知名诗人。在他最春风得意的时候,他也不怎么写评论文章,但是演讲越来越多。就像他喜欢高声朗读一样,他也喜欢演讲,在其中妙论迭出。就在《新罕布什尔》获得普利策奖之际,他把自己的诗学主张用一个个精巧的比喻扔给了听众。
“世上有两种现实主义者:一种拿出的土豆总是沾满了泥,以表明他们的土豆是真的,另一种却要把土豆弄干净才满意。我倾向第二种现实主义者。”
这是说,诗人要在揭示生活的时候“净化”它,既不能脱离生活或把生活神秘化,又不能让它像土地里刚挖出来的土豆那样,以“原生态”的名义粗糙不堪。他是一个十分节制的人,从未滥用自己的名声和财富,带着一支铅笔、用一把斧子在新罕布什尔开阔的田园里平静度日,是他留给公众的印象。他也喜欢用土地、作物来打比方,但是写诗又大不同于劳作。在另一篇文章里,弗罗斯特讲,很多人喜欢在春天看土地,看豆种如何发芽,但“诗人萌芽”的方式并不像豆种,而是更像海上的水龙卷:
“他开始时必须变成一团云,一团他所读过的其他所有诗人的诗形成的云。”
弗罗斯特极为看重写诗的终身性,他说,那就是水龙卷的方式,不断地吸收,一刻不停,以保持云的形成,从而得以随时降下壮观的雨水。有人问他,是不是写作无天分的人就只能做个好读者,他的回答总是“NO,唯有在写中读,在读中写”。在他近90年的生命里,新作始终不断,即便他爬满沟壑的脸,也是值得信任的土地和山峦。为此约翰·F.肯尼迪在就任总统时,把86岁的弗罗斯特请来朗读了一首新作。之前,肯尼迪已在多次演讲中用“还得赶好多里路才能安睡”作为结尾。典礼那天,在强风和阳光之下,弗罗斯特才念了几行诗,就放下了手中诗稿,转而即兴朗诵,在诗中,选民的伟大选择受到了歌颂,但是诗人也警告说,美国的成就,必须和殖民地以及内战的血腥往事相互“协调”。
诗歌中“骇人的东西”
尽管质朴清晰,诵读起来有民谣的韵律,可是他的诗仍然架不住要被深度分析,特别是在他1963年初辞世以后。重新盘点一个故人的人生,总会对其中悲剧感的因素投以更多的注意。因此,弗罗斯特的家庭悲剧——早年丧父,家族遗传精神分裂,亲生6个孩子只有两个是活了较长寿命的,其他的有的出生即夭折,有的在生产时病亡,尤其他的儿子在38岁自杀——就总也免不了被提及了。成名给弗罗斯特带来了他所渴望的一切,而生命中的无常,相当于上帝依公平起见而及时地做出扣除。

后起的批评家们若要捍卫弗罗斯特的地位,就得提供一些新说,以示他不那么传统,他是经得起阐释和发现的。1959年,弗罗斯特的85岁生日宴,“新批评”的头号大家莱昂内尔·特里林发表了一番讲话。特里林和老诗人是朋友,可是他的讲法不无故意显示深刻的嫌疑——特里林把弗罗斯特与索福克勒斯以及D.H.劳伦斯比较(“我跟这俩人有什么关系?”诗人想),然后说,弗罗斯特的诗并非清新幽默、通俗易懂的田园范儿,而是“骇人的”(terrifying)。
他举了一些弗氏诗中“基调阴暗”的细节。的确,如果只讲韵律优美,讲大众的喜爱,讲诗的“民族性”,那实在是老调重弹,非得说它们“骇人”,才像是更深刻。但是,骇人的东西,正如对生活之巨大悲剧感的体认一样,是必须存在于一个杰出诗人的作品之中的。弗罗斯特不喜欢这番话,一年后,在接受《巴黎评论》访谈时,他用他平素的快人快语说特里林少见多怪:“我纳闷,他怎么没早看到这一点呢?”
为证券之星据公开信息整理,由智能算法生成,不构成投资建议。
为证券之星据公开信息整理,由智能算法生成,不构成投资建议。
举报 文章作者
云也退
经济人的人文素养阅读 相关阅读 从韩江获诺贝尔文学奖,回看过去一个世纪的女性得主
从韩江获诺贝尔文学奖,回看过去一个世纪的女性得主在20世纪的100年里,女性获奖者只有区区9个人,起码有一半已经被遗忘。
351 10-18 10:50 约瑟夫·罗特:一个背井离乡、怀恋故国的世界主义者
约瑟夫·罗特:一个背井离乡、怀恋故国的世界主义者世界在解体,族群在互相敌对或是为利益而结盟,而罗特用写作抵御解体,他一手拿着烈酒酒杯,一手笔走龙蛇,收工之后还不忘在桌上留下可观的小费。
48 09-06 16:12 詹姆斯·鲍德温:破解性别和肤色神话的黑人文化明星
詹姆斯·鲍德温:破解性别和肤色神话的黑人文化明星鲍德温是美国的文化明星,在上世纪黑人文化的全明星阵容里,他占据一个无可争议的位置。
196 08-16 08:57 还原一个被焦虑、不自信缠绕的卡夫卡
还原一个被焦虑、不自信缠绕的卡夫卡谈论他成为一个符号,一个被消费的名字,一种能寄托许多情感的象征物,也是最常见的、很能显示作者阅历的缅怀卡夫卡的方式。
88 07-19 09:18 艾丽丝·门罗去世:她在世界一隅,慢慢挖出生活的奥秘
艾丽丝·门罗去世:她在世界一隅,慢慢挖出生活的奥秘当地时间5月13日晚,加拿大著名作家、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丽丝·门罗(Alice Munro)于安大略省逝世股票证券公司,享年92岁。
396 05-15 17:03 一财最热 点击关闭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,不代表十倍杠杆正规平台_加杠杆的股票平台_恒汇证券观点